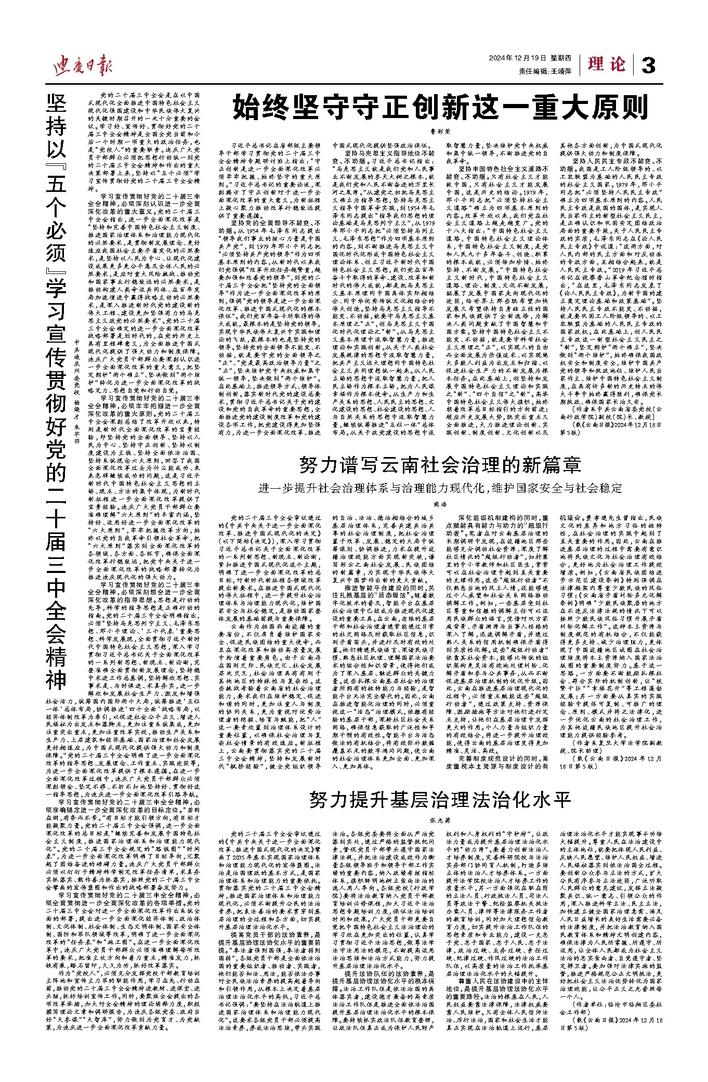
努力谱写云南社会治理的新篇章
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熊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新征程各领域改革提出新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推动国家整体发展的基础前提与重要保障。
云南作为祖国西南边疆的重要省份,不仅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而且在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云南存在国别交际、民族交汇、社会发展层次交叉,社会治理具有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些挑战考验着云南省的社会治理能力,要求我们在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与制度的协同关系,更为重视对优秀治理者的挖掘、培育与赋能,把“人”这一要素放置到治理体系设计的重要位置,以确保社会治理与复杂社会情景的有效适应。新征程上,云南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把社会治理置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力求在提升边疆治理效能方面实现新突破,谱写彩云之南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进智能平台建设的同时,关注扎根基层的“活态做法”。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智能平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已经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在云南,老练的基层干部和社会治理者通常能通过日常的社交网络及时获取社区信息,识别矛盾苗头,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置。他们精通民族语言、深谙民族习惯、熟悉社区机理、理解国家法治要求的综合性知识背景,使得他们成为了深入基层、触达群众的关键力量。这些扎根云南基层社会的治理者所拥有的独特能力与经验,是智能平台无法完全替代的。因此,云南在推进智能化治理的同时,必须重视这一“活态”治理模式,依赖有经验的基层干部,深耕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确保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早期干预的有效性。智能平台与活态做法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弥补数据覆盖不足的数字鸿沟问题,使云南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深化组织机制建构的同时,重点赋能具有能力与动力的“超级行动者”。笔者在对云南基层治理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在边疆地区那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深度了解社区情况的“超级行动者”,如村寨里的中小学教师和社区医生,常常可以在社会治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些“超级行动者”不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能够通过个人威望和社会关系网络推动调解工作。例如,一些基层受到社区尊重和信赖的调解主任可以运用民族群众的语言,凭借对双方家庭背景、矛盾渊源与当事人性格的深入了解,迅速调解矛盾,并通过熟人关系的信用机制确保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这些“超级行动者”依靠其社会资本,能够比传统的组织架构更灵活有效地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和参与公共事务,从而不断促进基层治理机制的优化升级。因此,云南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点赋能这些“超级行动者”,通过政策支持、资源保障、激励措施等方法对他们进行定点支持,让他们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个人力量与组织力量的有效结合,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使得云南的基层治理变得更加精准、灵活、高效。
完善制度规范设计的同时,高度重视本土资源与制度设计的有机结合。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地方习俗的独特性,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云南在推进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将民族文化与社会治理有效结合,更好地为社会治理工作提效增质。例如,《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特别强调在法律框架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云南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明确“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这种本土资源与制度规范的有机结合,不仅能获得更多支持、减少治理阻力,更体现了中国边疆地区试图在社会治理维度将本土资源纳入国家法治版图的重要制度努力。基于这一思路,一方面要不断鼓励扎根社会、符合实际的机制创新,让“枝繁干壮”“幸福花开”等工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要从真实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理念、原则、模式并将之法律化,进一步优化云南的社会治理工作,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经验参考。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载《云南日报》2024年12月18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