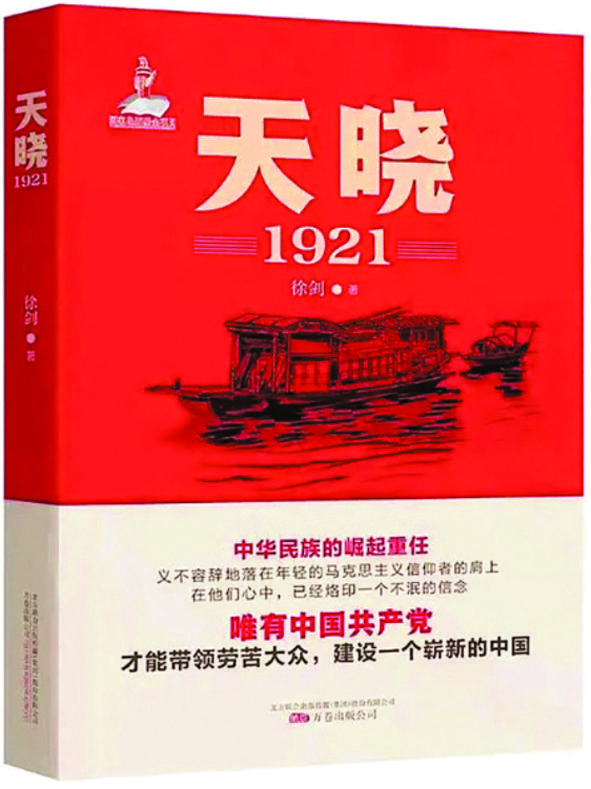建党历程的虔诚书写
——读报告文学《天晓——1921》
● 李 兴
近期,读了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深切感受了他虔诚书写的赤子情怀。作为出生于昆明的军旅作家,徐剑呈现出了对党的初心的致敬和文学初心的信仰。他的写作蕴含着对党的炽热深情,感情也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这书中的字里行间。
另辟蹊径的开篇,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史料的海洋波澜壮阔,都有导入的初源,一部好的作品,关键在于找到一把打开故事之门的钥匙。看了王会悟的口述资料,徐剑顿悟,这就是他要找的那把钥匙。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表,负责全力筹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工作的重任,而妻子王会悟则担负着大会召开的食宿、守卫工作。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她的叙述带着真实的个人生活色彩,也彰显了年代风貌。她回忆了与董必武、毛泽东等人见面的细节以及为“一大”当“哨兵”,后又安排转移到南湖游船继续开会的各种险情。作为“场内”和“场外”的见证者,王会悟掌握的信息远比任何参会者多,而且真实可靠客观可信。王会悟的口述无异于雪中送炭,使徐剑能够将历史的碎片一点一滴拼接起来,更好地展现了建党的辉煌历史。
科学的细节连缀,让历史活色生香。本书洋洋洒洒31万字,关于毛泽东的篇幅就达3万多字。徐剑对伟人心怀敬仰又目光平视,毛泽东既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既把毛泽东当伟人看,更把毛泽东当成一个鲜活的人来写。他曾4次去韶山,每一次都从不同视角有新的思考。其中,馆藏的4件旧物最为打动人,一件是毛泽东生命最后19个小时的医疗记录单、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一双棕色的两接头皮鞋,还有一件毛岸英穿过的衬衣。这些朴素的物件,触发了徐剑的情感,使他深切地感受了革命前辈的精神力量。
好的细节描写,可以使人物熠熠生辉。徐剑从毛泽东人生最后的档案记录,追溯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发展中历经坎坷、初心不变的心路历程,同时选取毛泽东的旧睡衣、珍藏毛岸英的遗物等片段,展现毛泽东“莫道英雄不怜情”的丰富情感。终章《归程·红船驶向百年》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李达的长谈,将此书的高潮定格于开国大典。细节描写是:“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那一夜一如从西柏坡进京前的晚上,毛泽东又失眠了。那天晚上,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来,吃了点儿辣椒拌豆腐乳,然后叫李银桥给他梳头。李银桥认为主席该睡觉了,结果梳完头后,他对卫士说:‘你这帮我一梳,足以坚持七八个小时。’后来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问:‘主席睡了吗?’李银桥说:‘报告周副主席,主席怎么劝也不睡。’‘这怎么行,明天下午是开国大典,主席不睡觉,身体挺不住啊。’‘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他吧。’周恩来果真来了,劝说了五六分钟,也没有用。等他走时,已经是清晨5点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天空发白了,李银桥进屋看,毛泽东才搁下笔,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独到的个性描写,让人物异彩纷呈。历史题材要想写出新意,既要沿着历史的时间隧道前行,又要力戒按照单一的线索直陈故事。把人物写活,才能使历史散发出应有的魅力。比如,陈独秀和马林两人个性几乎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便暴露无遗。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才情狂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却盛气凌人,对将成立的中共态度倨傲。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金等几项条件使陈独秀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与马林不欢而散。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又全力进行营救,花重金聘请律师出庭辩护,找铺保保释,打通会审各种关节,协助孙中山终使陈独秀出狱。此后,两人捐弃前嫌,虽在政见上仍有冲突,却保持了通力合作。如李大钊上绞刑架时,目光坚定,神色从容,身旁是两个一起赴刑的北大学生,徐剑虽然也交代了长达40分钟的三次行刑过程,但他却以抒情的手法和欢快的笔法,契合了李大钊慷慨赴死的决心。
在中共一大13名出席者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徐剑挖掘了大量史料。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徐剑致敬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回到历史中的位置。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徐剑看到他一度也在体制的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当时的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何叔衡参加“一大”时44岁,为参加会议13人中年龄最大。20世纪30年代初,何叔衡又远赴莫斯科留学。后担任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尺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江西梅坑,他与老友林伯渠道别,将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妻子弥留之际的唯一愿望便是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早在10多年前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
在描写陈潭秋时,徐剑面对展陈的一封托孤家书,文辞悲壮,句句直抵人心。因为参加革命,陈潭秋夫妇无法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就给老家的哥哥姐姐写了信,亲人对他们很不理解。但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中国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这样的走访、参观、阅读,徐剑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呈现给了读者。
对退出者和叛变者的客观对待,让史实不失公正。当然,还有像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尽管他们有的后来迷途知返,有的被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徐剑没有放过那些蛛丝马迹,通过不懈地追踪和翻刨,让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到了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历史。对他们的历史,在评价上可以褒贬,在定位上却不应该偏颇。对于这5个人,徐剑没有让他们成为历史的残缺。挖掘这些历史,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在书写革命者初心与人生时,不能隐去历史真实的一面,在“背叛者,失败者”这一章中,徐剑以“金陵,绝笔天叹欲无泪”“断崖千尺,沅江无声”“孤鸿楚天难归”等数节笔墨,叙写革命红船前行大浪淘沙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等人的另类人生和失色命运。
到湖北应城刘仁静老家采访时,当地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竟然不知道刘仁静为何人。如果不通过挖掘和存留,这些人的历史将会被漫流的时光和斑驳的岁月尘封。刘仁静在参加党的“一大”中年龄最小,当时只有18岁,是大家公认的青年才俊。刘仁静在会上兼任俄语翻译,他曾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又因赞成托派观点与党各奔东西。刘仁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1987年初被落实政策任国务院参事后不久,在街上被一辆公交车偶然撞倒离世,卒年85岁。在徐剑笔下,分明体现了历史的迷雾与个人命运间的悲剧性冲突,为人们完整理解一部百年党史提供了另一种参照。
徐剑在找寻大汉奸陈公博的遗痕方面也费了很大周折。他以陈公博被处决前的最后时光逆向书写,还原了他的惨淡人生。陈公博书法好,抗战结束后,被押解回国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转至苏州监狱,面临死刑之际,典狱长和狱警还不时向他索要“墨宝”。而陈公博在南京坐牢时面前的条案,竟是陈独秀当年坐牢时伏案留下过字迹的,陈公博曾来此看望过陈独秀。陈公博闻知后仰天一笑,深叹命运对自己的捉弄。通过回溯陈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脱党和追随汪精卫投日的经过,最后仍回到条案前,落墨写完最后一件条幅后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载《云南日报》2023年5月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