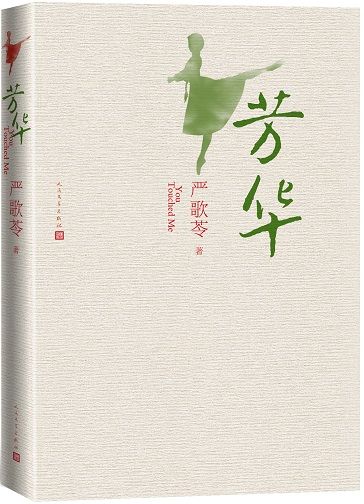|
严歌苓。摄影:周鹏 严歌苓又出书了!北京的四月春光短暂,在京城朝阳门街道27号院一处清静优雅的四合院内,一身紫色夏装的严歌苓妆容精致、坐姿挺拔,为新作《芳华》接受了记者采访。 每年保持出一本书的节奏,面对围观者的惊叹,她很淡然。“我不写怎么办呢?我读书的时间也留出来了,做饭的时间也留出来了,我精力大概太旺盛了吧。” 以前她的故事里总在写别人,这一次,她“触摸”自己。 小说原本叫《你触摸了我》,严歌苓的朋友将小说推荐给了导演冯小刚,结果看完后,马上拍板,决定改编成电影。他建议重起名字,严歌苓想了几个名字:《好儿好女》《青春作伴》《芳华》,最后用了《芳华》。 从军经历伴随了严歌苓整个的青春年华,她在军队待了13年,从1971年12岁入伍一直到25岁,整整跳了8年舞,最后却发现“我喜欢舞蹈,舞蹈却不喜欢我”,弃舞执笔,才有了今天的小说家。 细数她的作品《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白麻雀》《爱犬颗勒》《一个女人的史诗》等等,都取材于军旅,“写部队文工团我一直没有停过,那段生活对我太重要了,它左右我一生的走向。” 《芳华》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她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严歌苓化身为书中的女兵萧穗子,以她的视角记述、回忆、想像。 “这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采访中,严歌苓强调了好几次。
文艺女兵严歌苓 关于青春——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的一代人” 腿不是抬到最高的时候,摄影干事抓拍了这张照片。严歌苓穿军装跳舞的照片没留下几张,那时有严格的纪律,除了正式演出,不能随便穿演出服装照相。能看出来,当时的严歌苓二八年华,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我写这座楼,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脑子里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严歌苓称《芳华》是一次非常自然的写作。 严歌苓是出了名的勤奋刻苦,这种品格她自认为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写《小姨多鹤》,她专门跑到日本住进长野一个村子,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写《妈阁是座城》,为了刻画赌徒的心理,跑到澳门赌场掷金“体验”。写《陆犯焉识》时,又特地去青海劳改农场采访……但这一次没有,《芳华》的文字好像就生长在记忆的原地,等着严歌苓捡拾、组合。 《芳华》塑造了一组文艺兵群像。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芽。质朴善良的“好人”刘峰、因不良习气被集体歧视的何小曼以及林丁丁、郝淑文、萧穗子等情感的缠绕、交集,大相径庭又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他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有着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的一代人。”严歌苓在书中写道。她将“平凡即伟大”的极致倾注到小说中的“好人”刘峰身上,他超乎常人的心灵手巧、超越自我本能的善良和利他心,他以“模范标兵”的姿态在被需要中活得心满意足,却因一次“触摸事件”遭遇人生巨大转折。 这是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最直接地倾情赞美男主人公的一部作品,她自述也是代表自己以及同代人对当年的愚昧、浅薄深深的忏悔。这种自责缘于“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但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去爱他。你做好人在女性眼里是没有用的,你把他推到荣誉的高端,一切都是空的。” “青春就是充满的一段生命,每个错误最后都会来塑造你将来的人生。”严歌苓说。 关于爱情—— “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像力非常苍白” 快节奏掌控着现代人的生活,一切是速成的,一切也会速朽。《芳华》里那些缓慢、克制的爱情,那些耐着性子等待一个人成长、等待一次告白显得如此遥远而奢侈。 严歌苓感慨,现在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开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后凋谢也会很快。来不及品味,一天就匆匆过去了。“所以你读木心的诗,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谈起爱情观,严歌苓仍透着传统和浪漫。她觉得理想的恋爱是要会写情书,两个人要用心去表达,“情书都不会写,这是不是很大的遗憾?爱情的各种段落,你缺了很诗意的段落,那不很惨吗?” 在严歌苓看来,每张纸上写下的情书都是实实在在的,相当于白纸黑字的一种结盟,这是有意义的,就是在潜意识里一次一次确认这个爱情。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享受或者折磨没有经历的话,她不知道这个爱情怎么谈。 情书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上一部最接近她个人成长经历的小说《灰舞鞋》中,主人公小穗子因为在特殊年代160多封情书被曝光遭遇青春伤痛,这与《芳华》中的萧穗子遥相呼应。 严歌苓回忆起第一次谈恋爱,恋人是画家,他每次都画,收到的每一封情书都不一样,但是在部队里,管理很严格,能收到情书,“那简直就是你特别私密的一个盛大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这种活动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不知道。” 和先生1992年结婚之前,严歌苓还经常与他写情书,拿英文写。有一次在卧龙熊猫观察区,她发现当地红桦树的树皮很漂亮,就在上面写字然后寄走。“写情书你对纸张的选择,你对信封的选择,你会寄上一张照片,那是一种非常值得去体验的爱。” 反观当下,纸上情缘已经被邮件、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替代,人们的距离也许更近,但似乎也更远了。对电子类的交流方式,严歌苓保持着质疑态度,会用但不上瘾。享受在场的感觉,享受面对面的交流,她认为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 “爱不止是肢体,用手机发短信写情书,那是没有质感的东西,不高兴全删掉了,或者手机丢了都有可能。你真正一笔一划在上面,实实在在的宣言,每次都是山盟海誓,这比现代的手机要好。”但严歌苓说并不恨这个时代,也不觉得不可爱,只是可能缺失了一种诗意。 关于创作—— “你的眼睛要看得见所写的东西” 严歌苓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家。她与当代著名导演几乎都有合作,包括李安、陈凯歌、张艺谋、李少红等。 冯小刚也是年轻的时候入伍,并且同样进入了部队文工团。《芳华》与冯小刚记忆中的“青春”紧紧相连,他约请严歌苓亲自改编《芳华》的电影剧本,共修改了三稿。严歌苓透露,一共写了190场戏,多写了80多场。“小刚导演比较尊重我的独立思考,就是按照我的思路来写,他也比较好伺候。” 前段时间,电影《芳华》的初剪已经完成,严歌苓被邀请提前看片,观影过程中,严歌苓几度掉泪,她说,看这个电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被深深地打动。 读过严歌苓作品的人差不多会有同样的感受:文字的画面感强。很多场面像是电影镜头在运动,这是她的作品备受影视改编青睐的原因之一,《芳华》的开篇尤是如此。她认为,小说家应该能够把视觉等感官感觉放在文字里,让它更加有机,更加有活力,更鲜活一些,“你的眼睛要看得见所写的东西,我对自己有这种要求。” 身兼小说家和编剧,严歌苓并不认为这两种身份有高低之分,虽然现实中电影编剧的位置始终没有被看的很高。“但是电影剧本如果写的好,读起来一样非常有文学享受。有些电影剧本就像非常严肃的小说,里面的性格、对话,写的简直妙极了。” 严歌苓说,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运气,你笔下的人物忽然反过来惊喜到你。“我没有设计,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你当中埋了许许多多的逻辑在里面,到这时候他一定这么说的——他说完以后,这句话或者一个行为反过来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你写到最棒的地步了。” (文/王志艳) 来源:新华网 |
严歌苓:《芳华》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来源:香格里拉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5-03 11:46:11

频道精选
- 2024 年迪庆州新闻系列综合高级职称定向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区直通车:便捷出行,一站直达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区直通车:便捷出行,一站直达美景2024-09-05
- 张卫东到迪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开展调研2024-09-05
- 福彩代销者:增强责任意识 倡导理性购彩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庆人,这场活动需要您的参与!2024-09-04
- 积极参与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庆见义勇为”宣传募捐活动倡议书2024-09-04